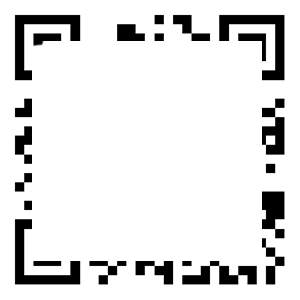趁着疫情趋缓,我就趁着空子去唐山找“五姐”。
“五姐妹”是一个年轻的家庭,他们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相遇。这家人姓张。地震中期,父母双亡,孩子成了孤儿。那时,大哥冯敏只有十六七岁。第二阶,他才十岁。
“五姐”其实是五兄妹,老大冯敏,老二夏风,老三李冯,老四五是双胞胎,老五是个小男孩,家里叫兔子。但是地震的时候,他们的孩子不断被人提起,都叫五姐。习惯了就叫“五姐”。一个或者五个姐妹,她们都知道那是她们家。
地震引发了一场自然灾害,把孩子们吓傻了。房子塌了,好好的一个家,第一天平安美好,到了早上就成了一堆砖瓦。父母被砸死,孩子不知去向,饿着肚子在废墟上徘徊。到时候,谁能控制谁。
三天后救灾部队来了,北京军区的炮兵负责自来水厂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。那时候,孩子们随意住在一个小棚子里,食物和饮料可以由街上的人分享。灾难来临时,哪里能有保障?饥饿和饱腹感。街道主任马也在为他们着想,可是生活这么难,又这么忙乱,怎么能体谅。
部队一到灾区,就摆在他们面前,帮助居民搭建简易房屋,从倒塌的房屋中寻找砖块,搭起墙壁,钉上油毡。谁能期待什么呢?有个窝就好。那一天,唐山下着雨,炮兵的肖先生挨家挨户到居民区,走进了张家。屋顶漏水,地下有水。孩子们惊恐地挤在一起。肖老师立即找到附近的二炮连,商量孩子的安置事宜。新盖的房子要地势高,质量好,邻居可靠,可以保护孩子的安全。新址选定后,第二炮兵连长甄带人施工。填一个大洞,拆一个马桶。冬天为了保暖,房子墙内外有两道栅栏,中间一层稻草,一层泥巴,一层石灰。为了牢固,所有的架子和木条都用手指粗的钉子固定连接。门窗都刷了漆,门前还铺了一块砖。在灾后的唐山,那几乎是最好的房子了。
以后的日子,张家五姐妹衣食无忧,二连垫底。连长甄肖鑫记得,孩子们会弥补他们的不足。在我孩子们的新家,我见过他们的月经和老姨夫。说起部队,哪个老人不感恩?
救灾部队在唐山驻扎到11月初,奉命撤离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,我赶到张的小屋和孩子们告别。小屋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,火光冲天,没有电。点燃一支蜡烛。冯敏不知道如何找到它,但也从倒塌的老房子里翻出了一套茶壶和杯子。火在燃烧,她不停地给我们泡茶。她拿出苹果枣,逼着我们吃,塞到我们口袋里。凤敏不停地哭,把眼泪抹到两边。过了一会儿,挂在我面前的头发粘成了湿湿的几绺。我们一直聊到半夜,然后起身道别。冯敏在门后追着问:叔叔,我明天能再见到你吗?他一头扎进甄连长的身体,放声大哭。他不停地哭。
寂静的夜空布满了星星。一个唐山女孩的哭声,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。每次想起都热泪盈眶。
第二天,我们的救灾部队撤离,唐山几十万人涌上街头,送别曾经生死攸关的亲人。在送别的人群中,我又遇到了五姐。就在这一天,五姐妹中最小的姐姐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“薛军”。那时候爱红、教育党、学习军队之类的名字多了去了。
离开唐山后,我和孩子经常有书信来往。有时候我会问他们的生活,他们也会聊他们的家。唐山地震后,最难过的是他们这种家庭。如果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孤儿,按照当时救灾的惯例,河北会统一把他们安置在石家庄等地。偏偏他们都不太大,说是成年人未成年人,或者说小的,也是青少年,上面还有他们16岁的大姐。他们也一样,不想分开,只能自己生火,一家五个孩子。
炮兵连队走的时候是初冬,连队给这个小家庭准备了被子,挂上了棉帘子。冬天烧完煤,存了白菜,几个战士甚至砍了足够他们冬天烧的柴火,堆在窗前。逢年过节,街上会派人送肉馅豆角,总会让孩子吃个饺子。远处,人们忧心忡忡。
一年后,炮兵决定让冯敏出去当兵。小女兵,开始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。后来,他被调到师卫生所学习化验。按照部队的想法,总是为了减轻这个家庭的负担,一个家庭少生孩子比较好。但是去接谁呢?一堆孩子太小,接不了老大。没有冯敏,四个孩子更难来。
夏风那时十四五岁,即将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。拿到粮面,去掉煤坯,去菜市场买便宜菜。偏偏最小的弟弟不懂事,觉得不好吃,吃完就溜了出来。夏风陷入了混乱,她只是哭了。你太坏了。你为什么不给你妈妈做饭?感谢上帝,你可以吃在嘴里。
当然,部队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小家。从连队到师里,不定期派人来看他们,带米线、萝卜、白菜。好在冯敏的炮兵师就驻扎在山海关,距离不远,来去方便。白各庄有个农场,离部队近,农产品有货就送。大家一条心,孩子不能再苦了。
1978年春节,张家五姐妹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节日。腊月,给街上的孩子发了110尺布票,20斤棉花,安排他们做了几件大衣,五双棉鞋。节前,炮兵把孩子一家接到军营,五姐妹和二炮连队官兵一起过春节。在过去的几年里,这很正常。有节日的时候,炮兵连会派人或者去接孩子。逢年过节,孩子们不能寂寞。了解所有细节的人说,这个家庭的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,但他们成为了军队的好亲戚。他们像“探亲”一样来来去去。亲戚,越走越近。来了又走,军人忘不了他们。老兵退伍了,所以来这里看看。新兵来了,知道连队有这么个亲戚,就接着认亲戚。在世界上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?一群陌生人如此亲密。
/p>
我1979年从部队转业,安置回山西老家。回山西之前,我想一定去唐山看一下。毕竟以后,从山西南部到河北东部,跑一趟不那么容易。
我从部队到唐山,又找到当年西北井水厂街,孩子们见到部队的客人,简直要喜欢疯了。凤霞总归不脱孩子气,可已经当起了这个小家。她叮里当啷和面剁馅儿,要给我们包饺子。我在部队做惯了那种粗犷的集体包饺子,也就不客气,和孩子们一起动手。我们的活儿做的实在可以说是不怎么好,可大家吃得满口香。那是一家小人儿接待远方亲戚的喜庆,味道儿自在心里。
我们依依惜别。又一次依依惜别。在水厂街他们的小房子前,拍了一张合影。凤敏已经当小兵去了,恰好孩子们的老舅来看望——这一带对于年纪最小的舅舅,习惯叫老舅——我们仍然五人,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旧砖头堆起的低矮的屋墙,四周都是黒油毡钉起的小房顶。门前一棵小杨树,一人多高。一条小路通过来,地面高高低低。1979年,整个国家正在一座巨大的穷摊子上谋划起飞,唐山,这一个曾经摧毁的城市,身边遗留下废墟的旧痕,那是再也自然不过。
我把这张照片保留在在身边,不想一过就是几十年。
在山西,我退休了,我老了,对五姐妹的思念却是日甚一日。我打定主意到唐山去一趟,看一看他们,也是了却我几十年的一桩心愿。
当年的公共汽车,早已变成了火车,又变成动车、高铁,三四个小时就到了唐山。冀东这一个因地震而成名的城,以崭新的面目迎接了我。几十年的发展,唐山早已消失了当年的一丝一毫的瓦砾痕迹,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。几十层的高楼鳞次栉比,无不炫耀着这个新生儿的着装与青春。下车一打听,唐山的房价比太原还高。听说在河北,唐山是排队仅次于省城的新城,发展进步令人咋舌。五姐妹植根在这样一处热土良苑,直教人无限的感慨,又无限的欢欣。
凤敏把我迎到老四凤琪家。凤琪日子好啊,住一座小别墅,三层,门楣上书“沁园人家”。有前院后院。进了里屋,落地窗前一面一根竖起大理石廊柱,一人多高的青花净瓶。沿着阶梯爬上二层,二层半缩,安装了一道浅黄色的石头栏杆。站在栏杆前,扶栏相望,可以俯视一层的客厅。厨房设置了整体化安装,如果包含地下,应该四层。墙体装饰全用石板,靠背长椅,大方茶几,一整套黄花梨木家具。所有这些,看样子是一个富裕人家的配置,五姐妹,你们都住进富人区不成?
凤敏接我,凤霞凤丽凤琪都在等我。凤霞的女儿开车,女儿的女儿也来了,在小姨家里蹦蹦跳跳。看样子,他们经常在这里聚会。
我们坐定,凤敏凤霞开口,叫了我一声:大哥——
我一愣,这个“叔叔”,他们叫了多年,今天这一声大哥,我知道岁月翻篇了。像是几十年的雨雪风霜脑子里又过了一遍,从地震现场回到了小别墅眼前。当年我是“解放军叔叔”,如今,五姐妹已经一个一个到了退休年龄,他们也走进老年了。
屋里就老五不在,我问,老五呢?
凤敏说,你问学军?他还没退呢,要上班。他最小,男的又晚几年退休。
学军?这就是当年那个乳名小兔的小弟。从1976哪一年,成了“学军”。
我们还说到肖师长王副政委,老首长都去世了。负责照顾姐妹们的跑二连连长甄小新,在北京开了一家医药公司,早已经做起了大老板,当年的军人,成了富翁一个。
当年的那一座油毡房呢,随着住房改善,早拆了。随着五姐妹一个一个结婚搬出,油毡房也越来越空,终于废弃了。相伴十余年,它完成了使命。门口那棵大杨树呢,早已经一人多粗,盖楼房没有留下。老地方,找不见了。
一开口,都是几十年的沧桑。
几十年的日子,凤敏在部队从军八年,复员后安排进唐山市妇幼保健院,仍做化验医师。凤霞凤丽他们姐弟,父母亲的单位接收了他们,他们都进了开滦矿。凤琪夫妇曾经做过几年销售,他们说,这一套房子,就是那些年的积蓄。现在,生意也不好。
我明白,他们找了一个最豪华的住宅接待我,还是想让我更多地看到几十年的明丽。其实他们姐弟几个,大多还是住那种小区单元房。和许许多多的唐山人一样,经历了生活的重建,以后他们各自结婚生子,走过人生四季。唐山默默地生长着大片的平常人家。几十年来,这五个小姐妹,就这样共同跨过了人生的低谷,填平了那个灾难的陷坑,一起成长,相互扶助,抱团取暖,最终都成了善良,大度,努力的好人。姐呀弟呀,骨肉亲情,慈爱平和,五家如一家。
华灯初上的时分,凤敏姊妹执意要拉我去当地有名的唐山宴。这一栋楼,是唐山文旅集团的旗下产业,也是一个领略唐山风情的好去处。进楼你就知道了,这里其实是一个楼中风情街,楼中馆驿,楼中历史博物馆。近代唐山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,这里铺设了中国第一条铁路,开动了第一列小火车,产出第一袋水泥。宽阔的走廊里,摆放着拼装的小火车头,开滦矿早期的传送带,煤斗子,仿制了都在身边。一楼是各色的唐山饭食,铺子方桌高靠背椅,店铺亮起招牌,渤海鱿鱼,京东肉饼,小山炸糕,全是早期的市井风味。一座戏楼高耸,台子上正在唱评戏,一股子赵丽蓉的口音。我们也上了一桌子唐山菜,不过想起来,我还是觉得那个贴饼子最有滋味。一口大锅,锅底添一瓢水,新鲜的玉米和面,拍成扁平,啪的一声贴上锅壁,又烙又烤,玉米的熟香溢散出来,那才是我记忆里的唐山美食。阔大的“唐山宴”招牌一边,附着一行小字——冀东情怀体验地,没错。
我们还站在一面唐山方言壁前,温习了几十年前,缭绕在耳边的唐山话。站在这里,水瓢,叫“水舀子”,小箩筐,叫“浅子”,顺便,叫“就手”,近些年流行的“瞎掰”、“愣充大尾巴狼”,这些都是早年唐山当地的说法。一边回忆一边学——唐山话发音说“小”——众人大的小的,禁不住放肆地大笑起来。
开心的唐山,开怀大笑的唐山,你,当年的苦难忘了吗?当年的悲惨,难道没有留下一点深的浅的痕迹吗?
有的。
我们在这里欢聚,凤霞没有来。
从一踏进张家的门里,我就发现凤霞的脸上始终罩着一层愁雾。说起当年,口气好像很淡,那可是他,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,一步一拔脚从泥泞里走出来的啊。姐姐去当兵了,家里由一个孩子带三个孩子。早年的烟熏火燎,肩挑手提,吃喝穿戴,都压在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孩身上,娇嫩的童年突然中断,支撑一个家,她是努断筋骨也只有硬挺。我们说起小五子嫌不好吃,饿着肚子逃饭出家去游逛,凤霞的眼里闪着幽怨,无奈地叹息——
他还嫌不好吃。那时,甭管生的熟的,能吃进嘴就不错了。
灾难,让凤霞缺失了一个完整的少年。过劳,让凤霞的身子一直拖着病。就在我们来这里欢乐聚餐,凤霞脸色苍白,送进了附近的医院。
灾难夺去了父母,也提前终止了一个少女花色灿烂的青春。这些年,她虽然也和常人一样走过了人生四季,早年过度的透支却是不能弥补。心上的伤,身上的伤,一直伴随着。风霜的痕迹写在脸上,灌注了全身的血脉。她是一个岁月的伤号。
1976年7月28日带来的一切,这一代唐山人注定要背负一辈子。
匆匆来去,匆匆话别。我就要离开唐山了。
凤敏凤丽带着我,来完成唐山的最后一瞥。我们当然要看当年的地震遗迹,地震博物馆。
唐山抗震纪念碑,建成于地震后10年的1986年。纪念碑坐落在市中心广场,碑座三米,碑身高30米。主碑由四个独立的梯形柱体组成,远远看去,如同伸向天际的四只巨手,象
征着“人定胜天”。碑身下部四周,由八块浮雕组成方形,象征着祖国四面八方对唐山的支援。不远处的抗震纪念馆,和纪念碑一个色调。突出英勇顽强,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,一场地震,就是一堂伟大的政治课,一曲嘹亮辉煌的战歌。
唐山地震博物馆,建成于2010年,坐落在美丽的南湖公园一旁。现在已经建成一处宽阔的园林公园。早先这里是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地震遗址。一进馆区就能看到,当年厂区的铁轨扭曲着,高大的厂房墙体垮塌,只剩下支撑房子的残破的框架在风雨里悲哀地兀立。馆区的门口有一群雕塑,再现了地震初期唐山人预制板下的挣扎。亲人压在底下,他们扭曲着面孔奋力搬扛,那脸上有死拼的抽搐,又有徒然和无奈。死者尸体在一旁倒着,丈夫悲戚地抚慰着妻子,小姐姐抱起更小的弟弟,残破的一家人恐慌地哭泣。更多的的男人女人光着上身,悲愤地望着苍天,谴责,怨恨,又绝望地低下头来。尸身就在一旁,掩面抽泣,失声哭嚎,那个残酷的黎明,让所有人参观的人群停下脚步,静默下来。
博物馆最凸显的建筑,叫做地震墙。一行排过去八座,每一座都10多米高,10多米宽,横竖划分成25乘15的方格,每一个方格,都密密麻麻填满了遇难者的名字。唐山地震,死难24万人,受伤16万人。24万个冤魂,他们的姓名一个一个嵌刻在墙面上。黑色的石板,正黄色的汉字。阳光扫过来,一排一排的魂魄像是知道我们来看望他们,争抢着闪射出刺目的眼神。行走在这一片惨烈的土地上,似乎能听到冤死的人们啾啾的鸣叫。沿着碑前大道行走,驻足仔细观看,可以看到,有的名字,已经抹去了,应该是误记了。有的名字某个字有改动,那是发现了差错,纠正过来。有的姓名已不可考,只能刻上某某之子,某某之女,等等。每一座墙体前,都有献鲜花的,也有按北方风俗摆放了纸扎,供奉了果品吃食。看来,地下亲人们,过生日或者其他纪念日,后人来常有人这里祭奠,寄托哀思。
唐山当地,把这个叫做地震墙。我想到了国外的传说,这一排黑色的高墙,还是叫哭墙吧。每年的7月28日,唐山人到这里痛哭一回,也算这个城市特有的哀鸣。
从抗震到地震,这个叫法的改变说明了什么?几十年间,国人终于能够正确地看待灾难。灾难就是灾难,没有什么抗震的伟大胜利可言。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一场惨绝人寰的人类大劫难。在以往,国人却几乎没有独立的灾难记忆,一般是或者有意识的遗忘灾难,或者以一种灾难—胜利的模式记忆灾难。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,国人都喜欢把抵抗挽救写成一场胜利。战斗—胜利,由是灾难的惨烈就被遮蔽。当所有的残酷绝灭一次一次披上了耀眼的红光,对苦难的歌颂就逐渐蔚成风气,这时,苦难的荒原上,一株怪异的花朵绽开了:多难兴邦。
那里是抗震纪念碑,这里是地震博物馆。抗震变成地震,我们不必再那样斤斤计较划分死者身份等级。纪念一场灾难,无论英雄和平民,都在国家的视野之内。每一个丧生的国民,国家都有责任记住他们。
我和凤敏凤丽,就在这长长的碑前大道,奔走,也驻足细看,找街道,找单位,找姓名,他们要找到自己的父母。地震以后,遇难的同胞统一埋葬,没有坟茔。在这个世间,黑色纪念碑上的两个名字,是父母留给他们的唯一的纪念。
我们仰望,像望天寻找,在24万颗星辰里寻找属于自己那一颗。我们搜寻,那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,街道门牌,星星点点,期待惊讶和悲情。
我在拜祈亲人显灵。哪一行金黄色的姓名突然闪出灵异的光,我们会扑上去,按住那熟悉的三个字,捂住那一小块石板,我们不能放手,一松手,那灵魂会轻轻飘起来,升空,从此杳无踪影。
24万姓名,哪里扫描得过来。纪念馆要闭馆了,我们只好失望地离开。
在门口,我们听到了寻找亲人的办法。唐山纪念馆已经把24万人的姓名地址全部录入电脑,划分好了区块。如果市民要来寻亲,输入姓名和当年住址,和哭墙的排名位置一对应,找起来应该不费难。
这个,只有等待下次再来。
那么小的三个字,那可是心头永不愈合的一道伤口。我还在期望,在幻想。一旦搜寻到那三个黄色的点点,五姐妹,你们每人一个指头肚儿齐齐地按住,那滴了40多年的血珠将不再滴血,那一道40多年未曾愈合的伤口,应该由此长住了。
我终于带着一点遗憾离开了唐山,离开了追寻多年的“五姐妹”。想当年,我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军人,五姐妹还是一群毛孩子。现在再来唐山寻访,一个战士和几个孤儿的故事,已经成了几个老人话当年。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,早年的那么一段命定的交集,竟然奇迹一般的保留到今天。人生的轨迹这样神奇,聚散无常,真实的情感,却是会跨越时空,某一个缘起,又把天南海北的人们招呼到一起,某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,有自己点点的牵挂,实在是非常可贵非常甜蜜的心事。
一死一生乃知交情。人类在灾难救护中结成的情谊应该永远不会褪色,不会淡化。千千万万个五姐妹,现如今,我们各自度过了不同的日子,我们各自走过了不同的岁月,无论世事如何日新月异,这一份旷世的情分不会变,这一份历史记忆不会变。1976年,恩情永恒。1976年,亲情永恒。你们的“叔叔”变成了大哥,依然会以一种老人的目光慈爱地望着你们。如今你们也长成了叔叔阿姨,1976年的地声地光,怪异恐怖,1976年的泼天大爱,山高海深。1978年的7月26日凌晨3点42分,从那一时刻起,注定我们的思念绵绵无尽。那一份血肉凝成的友谊,将伴随我们直到永远。
孩子们,弟兄们,姐妹们,请相信我。
(作者简介:毕星星,《山西文学》原副主编,著名作家,出版有著作多种,作品多次获奖。)
标签: